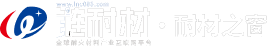“中國匯率制度改革有一種跡象在走日本曾走過的路��,這值得監(jiān)管層警醒���。”國務(wù)院發(fā)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日前在中央財經(jīng)大學(xué)演講時這樣表示����。
巴曙松指出,中國在面臨升值壓力時����,可以參考德國和日本的經(jīng)驗。當(dāng)時��,日本選擇的是“死扛”政策��,導(dǎo)致外匯儲備大幅上升�,最后一紙“廣場協(xié)定”形成大量的資產(chǎn)泡沫;而德國把匯率當(dāng)做一個市場工具�����,任其漲跌不顧,它所有政策的出發(fā)點都是本國經(jīng)濟的平衡�����。從實際效果來看���,德國的政策績效要比日本好��。
目前我國GDP僅占日本的1/3��,但外匯儲備卻已經(jīng)超過日本�����。我國經(jīng)濟發(fā)展中已經(jīng)形成了高速度積累的外匯儲備以及由此向市場投放的大量基礎(chǔ)貨幣�。巴曙松認為����,這些現(xiàn)象已經(jīng)顯示我們在朝日本的方向走,實際上我們應(yīng)該走德國所走的路�����。
巴曙松表示,要解決這個問題�����,我們應(yīng)該淡化匯率所承擔(dān)的政治任務(wù)�,應(yīng)使其回歸到經(jīng)濟杠桿的認識上來。匯率惟一的主要目標(biāo)就是要促進宏觀經(jīng)濟的平衡����?���!爱?dāng)然,基于中國金融市場發(fā)展的現(xiàn)實����,中國匯率的調(diào)整也應(yīng)采取漸進的方式?�!?
日元升值的前車之鑒
在匯率是否應(yīng)該升值方面����,日本是前車之鑒。上世紀(jì)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�����,日本鋼材、汽車���、機械和半導(dǎo)體的出口快速增長��,出現(xiàn)巨額的貿(mào)易順差��,這使得歐洲和美國的工業(yè)界深感不安�,并由此產(chǎn)生了不少貿(mào)易爭端�����。美國的財政部長們和權(quán)威人士常常威嚇日本讓日元升值�����。日本一方面正式同意“自愿”限制這類出口�����,另一方面默許通過日元升值來解決這些爭端����。結(jié)果從1971年1美元兌360日元一度上升到78日元����,近日也維持在117以內(nèi)���。尤其是1985年7月的“廣場協(xié)議”后��,日元對美元等主要國際貨幣不斷升值����,日元對美元在不足10年的時間內(nèi)升值了4倍多�����,日本出口產(chǎn)業(yè)幾乎喪失了價格優(yōu)勢����,不得不向勞動力成本更低廉的周邊東亞國家遷徙���,鼎盛的日本經(jīng)濟喪失了國際競爭力�����,最終陷入到漫無邊際的衰退之中��。
日元的大幅升值不但沒有消除日本的貿(mào)易順差�,在上個世紀(jì)80年代和90年代,日元的堅挺還對日本衰退中的經(jīng)濟強加了通貨緊縮壓力�����,并迫使其名義利率趨于0����。日本也因此掉入我們常說的“流動性陷阱”,貨幣政策趨于無效���。
日本的經(jīng)驗表明�����,政府在制定宏觀經(jīng)濟政策時����,應(yīng)慎重考慮貨幣升值問題��。日本在“尼克松沖擊”和“廣場協(xié)議”以后�,為應(yīng)對日元升值而采取的過度擴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導(dǎo)致了嚴(yán)重的通脹(1973-1974)和資產(chǎn)泡沫(1988-1990)等一系列經(jīng)濟問題。需要指出的是,“尼克松沖擊”以后��,日本政府試圖通過擴張的貨幣政策來抑制日元升值���;通過擴張的財政政策來減輕日元升值的通縮效應(yīng)�����。1972年的這種擴張性的政策導(dǎo)致了1973?1974年嚴(yán)重的通脹�����,在“廣場協(xié)議”期間�,日本政府放任日元大幅度升值�,同時采取貨幣財政雙擴張政策,以抵消日元升值的通縮效應(yīng)�,從而導(dǎo)致1988?1990年資產(chǎn)泡沫的產(chǎn)生�����。資產(chǎn)泡沫最終破滅���,導(dǎo)致上世紀(jì)90年代乃至進入新世紀(jì)的最初幾年經(jīng)濟的長期停滯�。由懼怕日元高匯價導(dǎo)致錯誤的宏觀經(jīng)濟政策,對經(jīng)濟的危害超過了日元升值本身產(chǎn)生的危害��。(北京現(xiàn)代商報)